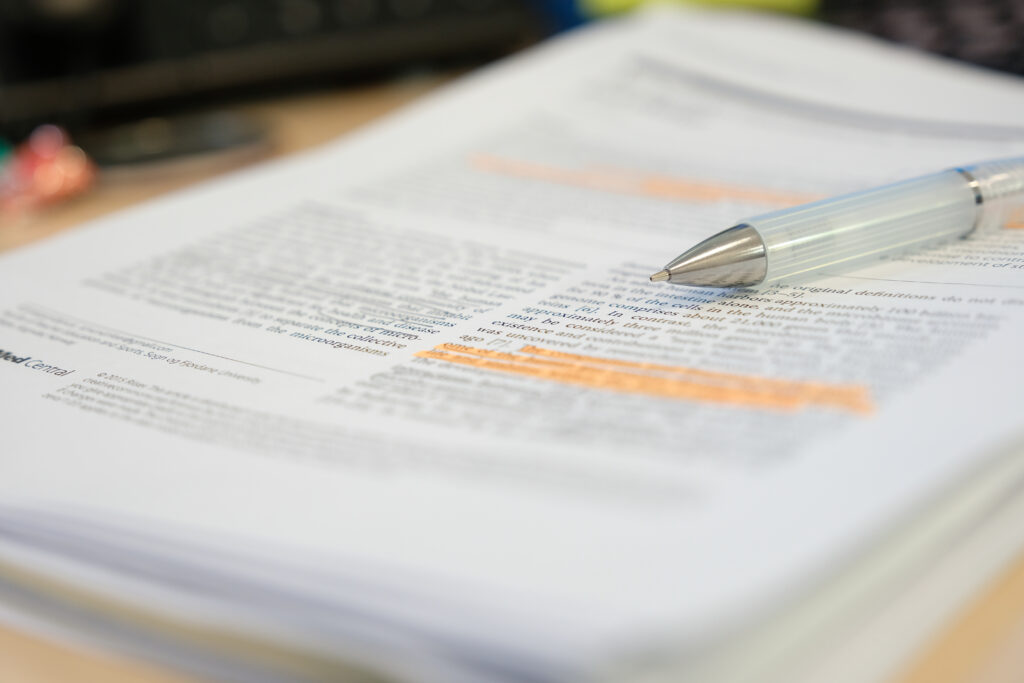卢跃刚|灾难报道:突破禁忌,报道真相

卢跃刚 |作家、知名媒体人
什么样的灾害信息有人关心?我们为什么会关注灾害信息,它触动了我们心灵当中的哪些部分?对于这个问题,新闻界的回答很简单,首先它是不是新闻。
新闻现在发生了变化,自媒体的出现使之发生了变化,即被分类、被结构化、被多元化。单一视角、新闻媒体精英主导新闻的时代结束了。所以说,我们现在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工具,利用什么样的分类来传播新闻。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主题,不展开说。
对NGO而言,要知道媒体想什么,结构性的、分类性新闻指的是什么?新闻在社会常理或制度限制里是逆反的,只要是逆反的就可能是大新闻。这方面需要NGO人士跟媒体人多沟通,好新闻、大新闻是在沟通里发现的。
我明天要讲到NGO的公共性问题。根据我的观察,壹基金这样的NGO做了很多工作,这些工作在我看来,对中国社会的建构无论是微观,还是中观都有重大意义。毕竟我参与了雅安地震灾后重建的全过程,之前也参与执行了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一些NGO项目,抵近持续观察到了一些现象。
今天,我讲的题目是,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讨论的大命题:新闻记者秉持什么样的职业标准,按照什么样的行为准则行动。
(一)灾难报道:突破禁忌,报道真相
要讨论灾难报道伦理问题的困境,其最大的困境是能不能报道。在中国语境下实现八个字——“突破禁忌,报道真相”,这是灾难报道伦理的第一点。
在中国语境下行动,有普适的意思,也有中国语境下的意思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,我参与了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(总编室夜班一版编辑)、1991年华东水灾、1998年大兴安岭火灾、1998年长江流域水灾、2003年淮河水灾、2003年SARS、2008汶川大地震、2013年雅安芦山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报道。
在中国讨论灾难报道的伦理问题,最大的困境是能不能报道。每个记者到现场去,第一是看,第二是进现场。看到什么?报道什么?就是实物实景。就其性质而言,记者在判断新闻的时候,进入灾难的时候秉持什么标准。
所以,在这个意义上,今天我这个题目是从两个层次来讲的。第一个层次,在中国语境下实现八个字——“突破禁忌,报道真相”。这是灾难报道伦理的第一原则。因为没有真相,其他什么都免谈。连及时传播灾难信息并进行有效的救助都没有,不要说认识灾难原因,更不要说一整套的社会救助、减灾防灾机制的建立了。
壹基金李健强刚才讲了海原地震和关东地震引起社会反思之别。日本是现代国家,有着高度发达的社会治理体系,对人类危害有着快速反应,东亚国家减防灾这套意识是从日本开始的,这说明了社会发育或现代文明发育的程度。
我明天会讲到从大地震也好、水灾也好、火灾也好,所有社会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,社会是如何反应的,反应到什么程度,效果怎样。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。
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伦理悖论。我们说的伦理悖论是指什么?我们经常讨论从越南的佛教徒自焚抗议到埃塞俄比亚大饥荒那幅“秃鹫与濒死儿童”的照片,此时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有双重角色,作为人的角色和作为记者角色,这就出现了伦理冲突,我把它叫做“职业伦理”与“社会伦理”的冲突,相当于韦伯所说的“责任伦理”与“政治伦理”的冲突,即作为一个记者的存在,同时也作为人的存在,专业选择和人性选择之间的悖论。
后边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适问题。我们现在报道的里边有,我本人也遇到过,但是相对于我提的第一个问题,我认为它分量稍轻,或者我们遇到的类似冲突没有那么多,因为那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个体人文价值高度自觉,对人的生命高度尊重、珍视的一个社会整体的反应。
而我们现在处于转型社会,一个比较幼稚的社会,有类似悖论,但是没那么突出。我们突出的问题是能不能报道,报什么,遇到问题怎么办,怎么规避政治风险,打擦边球。
比如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,我作为中国青年报总编室夜班一版编辑,一个月看不见前方火灾现场的稿子,大火烧得全世界都知道,主流媒体看不见,烧了一个月以后才有报道。我们刊发的《红色的警告》、《黑色的咏叹》、《绿色的悲哀》三篇特稿轰动全国,虽然报道全面突破了禁令,但是总结起来,也是后补的、总结性的、观念性的,而且是观念先行的报道模式。
最后从法律上而言,当时被批评官僚主义的林业局长案子都翻了。报道是有问题的,政治正确,政治性远远大于法治观念和现场真实,以社会的流行观念比如“改革”、“反官僚主义”去套报道灾难原因,弥补缺乏现场报道、信息不充分的缺陷。
图: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火灾,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森林火灾,又称为“无声的战斗”。
1991年华东水灾,我当时被报社委派中观协调报道,飞到长江和淮河流域。一下飞机就开始报道,但是也非常有限。很多重大的新闻,不准报道。刚下飞机就接到了中宣部的“八不准”——不准报道灾情,不准报道疫情,不准报道为什么……那去报道什么?
当时的中宣部某副部长是老左派,他在通气会上讲,记者没事生事,为什么要去拍淹没的民房,为什么要拍凄惨的画面。我一听到传达,就在电话里大骂,国内部负责水灾报道的副主任杨浪很有意思,害怕我骂人的内容外泄,做了一个决定,把我们之间的讨论内容从值班记录本删除。我们在电话里讨论的,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内容——新闻专业主义伦理问题。

1998年长江、嫩江、松花江大洪水,上面规定了一些专有名词,比如说“管涌”,出现管涌,报道时,只能说“出现险情”。“管涌”,就是洪水从大堤底部涌出的险情。管涌大,叫“重大险情”。故意模糊灾情,限制报道的准确性,误导公众的准确反馈。
还有,不准报道大堤决口,特别是长江大堤决口不准报道。当时《人民日报》有一篇报道吹嘘九江市防洪做得好,说“九江固若金汤”,挺长的一篇马屁报道。这篇报道发表没几天,长江九江段大堤决口。
这是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时最重大的新闻。中青报发表九江决口新闻是摄影记者贺延光写的。天大的新闻,当天央视不报,江西、九江所有的新闻媒体不报!伤天害理。中青报见报第二天央视才报,第三天江西、九江的新闻媒体才跟着报,九江城洪水滔天已经三天了。
突破禁令,九江长江大堤决口是一个标志,中青报第一时间现场报道是一个标志。所以当时有一句流传甚广话:大洪水冲破了九江长江大堤,中青报突破了水灾禁令“大堤”。虽然前期我们已经发了一个星期的水灾独家报道了。
报与不报,在禁令面前,对于记者,对于报社,是非常重大的考验。为了九江长江决堤报道,中青报负责报道的副总编在中宣部写了三次检讨过不了关。当然,一个月后形势突变,贺延光的报道获得了“九八大洪水”报道的特等奖。
图:2003年SARS事件
2003年SARS事件,最早先是南都开始报道,瘟疫接着往北走,北京已经泛滥成灾了谁都不知道。我有一个朋友的老婆是北京一个区防疫站的,说她供职的防疫站接到的被确认的SARS病人已有十多个,而媒体里面没有一个字。
为什么说胡舒立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记者、编辑,在历史转折这一刻,她做出了决定,她领导的媒体《财经》首先刊登SARS的消息,突破了禁令,维护中国新闻界应该有的专业主义伦理和职业尊严。《财经》报道后,紧接着美国《时代》周刊,再往下就是《三联生活周刊》,全面、充分地报道了SARS。
禁言、突破、挨批、否定、肯定、再否定、再被肯定,一篇好的灾难报道,都会经历这样的轮回,这个过程对于一个成熟媒体或者负责任的媒体而言,作为成熟的记者或者有抱负有追求的记者而言,我认为就是不断坚守新闻专业主义伦理的过程。
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。无论我们有失误还是成功,我们是有案可循的。SARS是1949年以来中国遭遇的最大的一场瘟疫。作为世界的一种新的病毒,我们专业知识不具备。
我花了大工夫,在家读了一个多星期的世界流行病史,读完一下就明白了。第一是找到病原体,第二是病源隔离,第三是了解已有治疗手段是否有效及是否发现了新的有效治疗方法。结论是:人为制造的恐怖,包括向公众封锁信息,远超过了瘟疫本身对人类的威胁。这样的话,我们就能制定科学的报道策划,配置报道资源。
(二)灾难报道:专业伦理优先
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拆解社会、破坏社会,使得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不像专业人士,专业没有标准,不以维护这个专业的伦理成为有所作为的恪守准则,这是我们社会的病根所在。
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演讲,标题是《没有分工就没有正义》,就是讲分工理论支持的专业主义伦理问题。正义跟专业分工挂钩具有最原初的意义,是柏拉图建构的。柏拉图是正确的。
中国社会最大的弊端是拆解社会,破坏社会分工,使得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不像专业人士,专业没有标准,没有专业伦理来约束人的行为。
比如SARS,首先是专业问题,即流行病学的问题,传染病学的问题,其次才能是其他的问题。防范它,认识它,人类没有经验。这是一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战争。
观察广东的措施,北京的措施,4月20日开始公开报道,我认为一个月的时间,即5月20日以后疫情将会得到控制,患者曲线会持平,然后逐渐下滑。我这个判断说出来,很多人包括我的同事取笑我,因为那时正是恐慌高峰,北京空城,全国围追堵截北京人。
我判断的依据很简单:1、病原体已经发现并被命名;2、北京小汤山隔离医院建立,已经实现物理隔离;3、钟南山在广州中西医结合,已经有临床治愈案例,北京的相关医院也有临床治愈案例;4、持续上升的患者曲线,是因为前期患者没有得到有效统计,或一些病人没有得到确证所致,当然也有新增患者。
人类历史上有一套预防社会瘟疫的方法。我们批评政府的时候,不对的是什么,对的是什么,这是一个科学问题,专业问题。专业问题包括两个方面,一是新闻专业,一是流行病和瘟疫的专业知识。
从正义的角度,灾难报道的第一条原则,必须是也只能是“揭示真相”。怎么报,是另外一个问题,再讨论。
第二个问题,灾难报道现场,社会伦理与新闻职业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,我的观点:职业伦理优先。
我的理由很简单,一家媒体派出自己最优秀的记者,赴灾难前线采访、报道,媒体在这个时候为你最大程度地配置了资源,对于媒体而言,它只有一个要求,写出一流的报道。因为广大的读者、观众期待着一流的报道。
这是个多维度的问题,实现职业伦理的过程,是一个结构(各种资源的配置)、一个流程(新闻生产的每个环节),不是单纯的记者个人表现。这跟社会有关,跟媒体有多重功能多重属性有关。媒体,既有社会公众性,也有企业私利性。
我们看到很多案例很悲惨,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的案例,拍《苏丹的饥饿》的那个记者后来自杀了。我分析这个案例,有“道德自责”的情景。
图:曾获得过普利策奖的摄影作品《苏丹的饥饿》
自然灾难的报道,也会给报道者带来严重的心理问题。汶川地震后,南方都市报2008年在人大做过一次灾害报道的论坛,我有一个发言,主要内容是呼吁建构“灾害心理学”,包括回答2008年很多记者看到灾难现场以后的悲痛欲绝,被摧毁了作为这个职业的合理性或者作为人的合理性,即所谓“灾害心理创伤”,包括灾民的生活。但是,我的呼吁,心理学界的回应是非常微弱的。
灾害心理在我看来是一个理论,并不仅是一项简单的工作,不是实务,是理论。研究不同族群,不同地区,不同国家,在自然灾害面前的社会心理反应机制。包括新闻记者,我读了很多案例,在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之后,有记者看到现场后心理崩溃,心理学家也有跟记者谈,也有记者因此辞职。
对于第二个问题,今天尚未定论。不过,在我这里:职业伦理优先。
会场嘉宾讨论摘取:
破坏社会与拆解专业带来的后果——
龙科(原《中国财富》主编):
非常感谢卢跃刚先生的演讲,我是第一次听卢先生演讲,以他业界的经历,始终秉持他个人作为人的专业体验过程。我个人觉得非常受益,接下来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跟卢老师对话,把你们的问题抛出来。这个主题非常有开放性,而且可以跟我们每个人联系起来,我们谈到伦理的时候它不仅跟人有关,而且跟我们从事的工作有关,是带着某种信仰、文化和体验的过程,这样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有想表达的。
王天定(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):
卢老师刚才讲的中国社会的病根问题,我也有一个观察,咱们中国现在没有哪一个职业能够真正让人尊敬,可能很多职业让人很羡慕,但是发自内心让人尊敬的专业没有,为什么中国社会会这样?
卢跃刚(作家、知名媒体人):
这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,因为它确实涉及制度结构和统治方式。我们在现实中能够看见,就是当教授不把好教授作为标准,当医生不把好医生作为标准,当记者不把当好记者作为终身追求目标,当法官不可受法律而是听命于权力……法官涉及正义,教育涉及人心,新闻报道涉及历史,医生涉及人的生命,都是社会最重要的部分出问题。后来,我们发现,让社会碎片化是一种控制方法,从社会转型看,从历史角度来看,他们肯定认为这是有效的,我刚才讲了破坏社会和拆解专业带来的后果很严重,即社会的溃败。现代社会有一个基本特点,它是由一整套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建构起来的,无论从社会治理结构理论,还是社会分工体系,都是现代社会的标志。根本不用讨论,是不是好记者一眼便知,是不是好医生一眼便知。可是好教授呆不住,好医生呆不住。为什么?
为什么社会出现了巨大的结构性的制度性的逆淘汰。从分工理论来讲,如果没有分工,没有社会治理的专业的行业的自律分工这套体系,就不可能存在社会良善。这是肯定的。
胡舒立讨论《新快报》陈永洲案时,提出第一点就是“自律”。没有纠错机制,没有庞大的同业制约,或者没有标准,有标准也不稳定,那么整个社会的环节是松扣的,是可左可右的,是可正可反的,是可黑可白的,充满了不确定性,而不确定性或故意制造不确定性就是当今社会治理的真正病根。
刘万永(资深媒体人、《仟言万语》创始人):
我想问一下卢老师,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,我觉得这两年来关于媒体的争论特别多,比如马航,记者说是不是要到现场去?你去采访,到现场就是到酒店,家属在那里,拿着照相机摄像机采访是不是造成二次伤害,这个争论就很严重,业内某些报道就会出现争论,比如后来庞麦郎的报道,报道会分成两拨,这是为什么?
卢跃刚(作家、知名媒体人):
我有微博,从来不写一个字,微信上来以后也非常勉强,但是我上了微信以后,整个把我对中国社会、中国乡村和传统这块的东西一下看清了。原来我对这些新工具完全是排斥的。我的新闻专业主义标准是原教旨的,总体而言比较保守。我认为故事是猜不出来的,一个故事要写出来,当下人类的行动还很难用千里眼顺风耳的方法来完成一次有效的、真实的、有细节的访问。第二,从人类思维方式来讲也是这样,有些问题片刻可以反映,一些问题要一系列的碎片连成,这是一个过程,一个时段,而不是一个切片。
实际上,在这个思考的过程,也需要有一部分人认真想清楚一两个问题,在我看,一生想清楚一两个问题已经非常不得了,而这一两个问题想的方法一定不是随机的。
我想说的是,新闻制作的过程,现在虽然已经工具化了,多样化了,结构化了等等,仍然不能回避的是,有一些重大的问题,重大的现象,需要有人持续关注和访问。
像马航,我觉得一个好记者不是面对采访对象,骚扰式的访问不能获得信任。我看所有的好记者,无论国内外,我见过没见过的都有一个特点,特别是深度报道,与被采访对象之间,都有逐渐互相信任,然后拿到独家材料的过程。
而这个过程不是那一刻就会告诉你,人跟人交流不可能是这样,特别涉及一些具有公共价值的隐私,这是人的交流过程。
从有效交流而言,我们老讲有效采访,采访说的话很多,是不是有效?那不一定。所以,我明天会讲到这一点,就是灾害救助的伦理问题,如果不建构社会的平等对话体系,修复或认知灾害救助主体,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交流的话,不可能有效地去帮助别人,同时帮助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