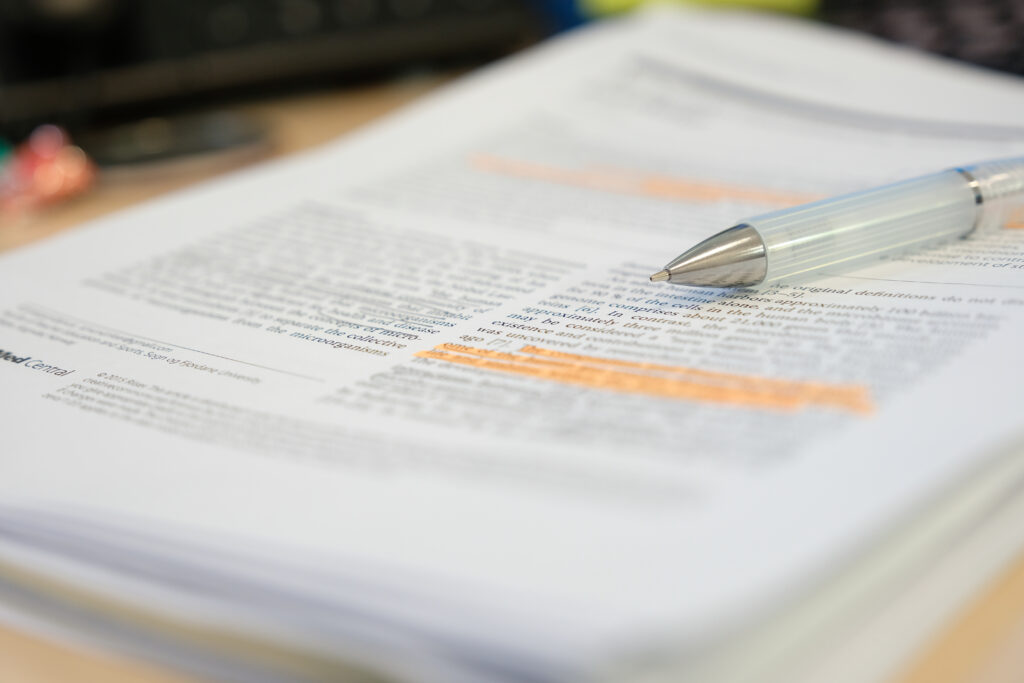拒绝商业资助 他运营一家只有调查记者的通讯社
传真社(Factwire)是一家位于香港的非营利调查新闻通讯社,由资深传媒人吴晓东通过市民集资的方式创办,于2016年开始运营。他们专注调查性报道,发表的文章多获各大主流媒体采用。
创立初期,吴立下众筹三百万的目标,这本是一个“mission impossible”,却意外在短期内完成了,吴当即激动落泪。前CNN数字亚洲项目主管Marc Lourdes采访了吴晓东,想搞清楚这种甚少成功的新闻编辑室模式,到底是如何推行的。
在一个媒体失信的时代,香港的传真社在创业初期阶段就众筹到了60万美金。他们有个很简单的目标:做基于事实、不带个人观点、不掺杂商业或政治利益的调查报道。
创始人吴晓东想建立一个像路透社、AP和AFP一样的通讯社,让香港人读到不带偏见的调查报道,这样的报道在主流媒体中已经很少见了。
吴打破了新闻编辑部长久以来形成的层级制度,只在团队中招纳记者,省去了编辑的职位,让记者们相互点评相互编辑。
他们要呈现的成品是一种“回归初心”的新闻报道,用最基本的原则和技能进行新闻写作,不哗众取宠。不过,这种模式下的传真社似乎很难在当下的环境中生存。
我约了吴先生见面,想搞清楚这个独一无二的通讯社是怎么运营的。
Q:为什么要创办传真社?
吴晓东(以下简称”W”):现在敌视媒体的情绪很普遍,我在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。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的信誉被毁了,为什么人们不再相信记者了。我的结论是,个别媒体不再是“公正”和“独立”的了,这让公众(对媒体)有了不太好的印象。
我想,如果能做些什么来挽回(公众对媒体的)信任,那必然非创立一个媒体莫属了。它必须是独立的,资金来源不是商业化的。
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场难打的仗,但是几个月的运营后,99%的香港媒体,不论是网媒还是主流媒体,都订阅了我们的新闻。这令我特别惊讶。每次传真社发表了文章,99%的香港媒体都会采用。
Q:为什么起点会这么好?你填补了什么空缺?
W:香港的媒体大多都有局限性,很多媒体不会主动去做调查新闻。所以当像我们这样的媒体做了,他们就会使用,他们可以说这是传真社做的,不是他们做的。
Q:在香港运营媒体有多难?你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挑战?
A:在成本控制方面比较困难,因为我们给调查记者开的薪水都不低。另外在香港,租赁办公室也是很贵的。曾经有人提议要给我一间免费的办公室,我们拒绝了,因为我们想保持独立性。
迄今为止我们没有任何收入,主要的运营依靠社会捐款。
我们经营的产品不是文章,而是使命感。大家给我们捐赠资金,不仅仅是为了阅读我们的作品,他们更想得到的,是共同为建立一个独立媒体机构出份力,把这个使命传递下去。
我们的记者之前有过一些讨论,比如我们是否应该多写些大家爱看的,关于公众利益的报道?或是我们是否该建立一个支付墙?
最后我们发现,人们给我们捐赠并不是因为文章写得有多好——在香港,如果你想读到好文章,很多平台都可以提供。因此,这种使命感才是说服他们捐款的主因。
我们目前正在尽力众筹,现在每个月,都有252人为我们捐赠25港币。如果这个势头变好,我们就会有稳定的资金来源,招更多的记者,写更多独立报道。到那时我们还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商业模式,比如说让企业订阅,或是发表新闻简报。否则的话,它就只会变成一个公共服务,依赖社会的捐款。
Q:除了调查记者,你们机构还有什么职位?
W:我们有七个记者,一个信息搜查记者。其中两个记者是双语记者,其他则只用中文写作。我们当中没有编辑。假如有一篇报道草稿出来了,记者们就要互换职责,一个人写,另一个就帮忙编辑,再来一个做事实核查。所以,其实每个人都有编辑、校对的工作职责。我们是一个互助式编辑部。
Q:谁来负责领导运营?
W:我们的新闻编辑部目前还是实验式的,记者们得自己管理自己的工作,我们没有上下级之分。假如要做一些内容上的决策,他们会自主投票决定。如果某篇报道存在特别大的争议,那就少数服从多数。在经营方面,他们会听取我的意见,比如说,我们需不需要更换办公室,要不要裁员。
Q:你的职责具体是什么?
W:我在众筹时就承诺过,我不受传真社雇佣。我只是一个发言人,募捐人,一个负责面对公众的人,因为很多记者不希望把他们自己曝光在公众视线里。我不干涉编辑组的运转,但是会每个月与记者们开一个会,了解情况,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在。
Q:你们做调查报道时使用什么工具?
W:我们使用Whatsapp和Telegram相互沟通,和公众互动,大家有什么料也会通过这些平台传给我们。记者当然也会使用他们自己的人脉和资源。
我们的新闻风格是非常传统老派的。大多数时候,记者们会出去实地采访,和人们交谈,或者约访。有时候对方不愿意接受采访,我们的记者就在那个人(公司或住处)附近苦等几个星期。另外,记者们也会去找各类文件,给政府部门发送邮件,申请信息公开。
Q:最后一个问题,很多适用网络平台的媒体都用流量来衡量成功与否,你们怎么衡量自己的业绩?
W:一个标准是多少媒体会采信我们的报道,另一个就是脸书上的读者反馈。
很多香港读者会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上读我们的报道,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官网上,所以官网的流量非常低。我们会在报道发往不同媒介的六至十小时后,把它传到官网上。
我们并不依靠广告和点击率存活,流量对我们来说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有多少其他媒体转载或采用我们的报道。
编译/Lizzy Huang
编辑/Ivan Zhai
相关阅读:
Bridget Gallagher:非营利组织的募款之道 | 深度报道锦囊
BuzzFeed调查报道主管:90%成功的调查报道源于选好故事 | GIJC17

本文首发于The Splice Newsroom官网,全球深度报道网经授权转载。Marc Lourdes是一名资深记者,曾任职CNN数字亚洲项目主管。此外,他在Yahoo!工作过五年,在The Star以及《新海峡时报》做过十年记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