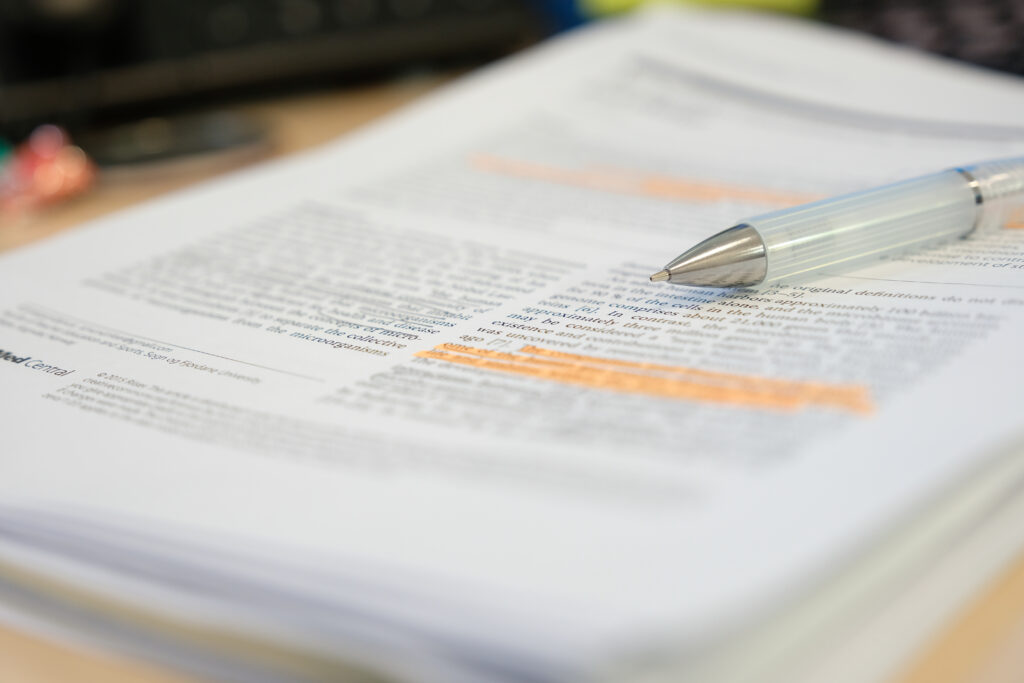30年资历,从地方记者征战到世界一流媒体工作,再到跟不同编辑台打交道,张彦说他在地方报纸的工作经验锻炼了不少能力。(蔡耀征摄)
编者按:普利策奖得主张彦(Ian Johnson)的作品《中国的灵魂》(The Souls of China)最近出版了中文版,台湾非营利网络公益媒体“报导者”总编辑李雪莉与张彦进行了专访和对谈。除了刊载在“报导者”上的访谈文章以外,李雪莉也在自己的 Medium 分享了她与张彦在田野技巧上的切磋。全球深度报道网经授权编辑转载,内容有部分删节。
57岁的张彦,记者生涯比我多了10年,记者采访记者是个很有趣也紧张的经验,我们清楚记者的起手式,可以嗅出问话背后的议题设定,采访结束大概也知道文章可能会怎么被处理。
我还记得那天进入正式访谈前,傍晚四四南村的风开始吹了起来,我们想趁外头还有光线时,请摄影师耀征先帮张彦拍照。我还记得出版社的家轩体贴地早我一步站起来,想让我静下来准备待会儿的采访,由他陪张彦拍照即可。但我其实有习惯跟着受访者一起拍照,尤其是第一次见面,总要先熟悉彼此,顺便找些话题。有趣的是我还没开口,张彦就直觉地向我招手,然后对着家轩说“让她来吧”。
这句话让我意识到,我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随时 ready 的记者。我想张彦很清楚,记者的采访不是在坐着面对面访谈时才开始的,走路、坐车、吃饭、趁摄影拍照时,都是对受访者观察的好机会。于是,在拍照时,他跟我指着四四南村旁的大楼说他1986年来台北时的记忆;采访后我们一起搭出租车到下个地点,因为够接近也够放松,我看他打着呵欠,身上飘着淡淡琉璜味,他就跟我多说了这回其实不是住饭店,而是待在老朋友、前《人间杂志》摄影钟俊升在阳明山的家。
很多互动和好材料,都不是在硬梆梆采访那刻开始起算的。
张彦没有向我要求提纲,这位资深记者说他最讨厌别人先要提纲,他知道“记者希望更自然的回应”。那天,中文挺流利的他夹杂着中英文回答,当我发现他说英文更为直觉、精准,语速也更快时,自然请他多说英文,我想,让受访者使用一个让他自己感觉聪明俐落的语言,也是很重要的。
张彦待过 《巴尔的摩太阳报》(The Baltimore Sun)、《华尔街日报》(The Wall Street Journal)、《纽约时报》(The New York Times),2010年开始成为一名自由作家。30年资历,从地方记者征战到世界一流媒体工作,再到跟不同编辑台打交道,张彦说他在地方报纸的工作经验锻炼了不少能力,而在对谈和采访中,他更分享了自己如何锻炼田野的能力。
我不确定这些内容是不是适用每个人,但至少对做记者工作20年的我来说,还是有很多的提醒。尤其当我们面对一个极陌生的环境,或是巨大的国度,写作者怎么在茫茫大海中寻找问题意识?如何和陌生的他者建立信任关系?又怎么超越种族、性别、国族、地域、身位、社经地位、宗教信仰、生命经验、道德与价值的各种差异,让对方感觉被尊重、愿意掏心掏肺?这一直是写作者最重要的功课。
我对张彦的专访已在《报导者》刊出,以下是与他访谈内容与对谈现场的遗珠,文中我适时加了点小标,做点归纳。希望看到的人能从这些细节看出好记者怎么练就的。
问:你的写作风格看得出有非常仔细,像照相式的纪录、厚描的能力。这个能力是怎么培养和练习?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你必须时时做纪录?
张彦:年轻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个经验,我当学生时去了北京白云观,我没想到它会改变的那么快。我会希望当时我拍的照片多一点,虽然那时候不是数字时代。
我意识到必须时时做记录,是在柏林。我1988年去柏林,去东德、东柏林几次,觉得虽然东欧的、波兰那些国家有些改革,有些团结工会出来,但东德肯定不会改变。没想到,一年之后东德就没了,两年后这个国家不存在了。所以我发现世界局势能改变得非常快。
问:你在许多国际级的媒体工作过,而你第一份工作是在洛杉矶的《奥兰多哨兵报》(Orlando Sentinel),那份地方报纸的工作经验对你有什么影响吗?
张彦:我觉得地方报纸让我写新闻更为谨慎。其实地方新闻是困难的,因为当地的人们会阅读你的文章,而且报纸出刊后的隔天,他们看到你时可能会说“你写得很糟!”地方新闻很有效果、也有实质影响力,但写国际新闻,唯一的影响是你帮助人们了解事情。
但现在洛杉矶的媒体也不再采访学校董事会,《洛杉矶时报》(Los Angeles Times)从前在加州南部有办事处,现在都关了。整体来说这是个问题,民主会萎靡在黑暗之中。
消息多、交通方便,但田野却愈做愈少
问:做为一位记者,你田野的量与质非常惊人。你如何在日报工作,又能花这么多时间做田野?
张彦:我在中国有个原则,有点理想的做法,就是每个月,最少有一周在北京之外。中国很大,不能老在首都。一星期在外面听起来不多,但要准备采访、准备飞机票,还是挺多事的。
还有不要老跟别的记者在一起,这是很大的问题。工作12小时,再去酒吧跟记者喝酒,白天在办公室写东西,记者们不太了解外面的世界,都在小小范围。
记者采访的太少。就像大家说的“三个就成趋势”(Three is a trend)。这是有效果的记者,采访少,写快写多,但这样的工作不一定是好的,会学不到东西。另一个更重要,我会看学术的材料,我发觉外国记者很少看学者的研究,这很可惜。
25年前要去新疆南边不方便,但现在去很多地方很方便,大部分记者却待在北京,或出去采访时间非常短。以前去新疆南边要花一周或十天,但现在可能去最多待两个晚上,第三个晚上就回到家了。在网络世代,很多人开始采访时已经知道想写什么。
以前在《华尔街日报》,一个资深编辑告诉我,在一个地如果要采访3天,至少你要待4天,采访完要再去走走、散步、看东西,那时你的脑子是最开放的,你会碰到没有想到的东西,这可能是新闻。但现在编辑都在网上看东西,他们会说在网上看到什么,要你去报导。我觉得现在很多采访与记者的工作像是个回音室(echo chamber),你说,我听,然后我也说(一样的),来来回回,但真的了解与深入报导却很少。消息愈多,交通愈方便,但去做田野的却愈来愈少,田野的工作就变成文章里一个小小的部分。
特别是老百姓的生活,你得花很多时间。老百姓跟知识分子不同,知识分子会自己描述自己的生活,有自我意识,但很多人没有,你必须跟他们一起,去看他们做什么。你问他们信什么宗教,他们说没有,做调查问他们是佛教徒还是道教徒,他们说什么都不是;但如果换个方式问有没有信仰,他说他有信仰。跟他们在一起进香的15天,你才知道他们是有信仰的。所以要一直在一起,才能理解。
问:为什么是去15天,而不是去10天?
张彦:我不是很有纪律,但喜欢回到田野里面。我没有每年去香会,但去一次就想待完全程。很多人来待一、两天就走了,但受访者会说些事情,你待愈久,愈跟他们聊,他们就会告诉你更多的、真正的事情,他们会更信任你;采访的时候你可以观察、看到更多严肃的东西,如果你表达你的真诚之意,花很多时间,不管是在哪里,人们都愿意对你打开心胸。
问:你会怎么描述你的田野方法?
张彦:参与观察者(participant observer),我有时看,有时参与。我也修练。
为了解道教的内丹术,我去浙江金华的山洞里摸黑体验打座,每回10天;我在北京,跟着香会上妙峰山,有次练棍的师傅对我说:“你老问那么多问题干嘛,应该自己下来练,才会更清楚我们的信仰。”所以我开始练棍,参与他们(张彦拿出手机,秀出他今年农历年在庙前跟一个道士打斗的影片。他说这是一个“套路”,然后夸了一下自己打得不错)。
作为一位自由撰稿者,如何跟不同的编辑台合作?
我刚到大学时,我要学记者,有个《华盛顿邮报》(The Washington Post)的高级编辑到我们学校演讲,他说记者不是学习,而是实习,不是 academic(学术)而是 practice(实践),你去好的编辑部工作是最棒的。所以我大学去学了中文。
我觉得在工作时我第一个学习是,“听领导人的话但也不听领导人的话”,因为编辑们经常有自我矛盾的东西,大部分编辑的想法是要记者多写东西,希望记者有效率、效果,但又想记者可不可以也研究个题目、得个普立策奖嘛!这是编辑部的 stupid 的 ideas(愚蠢的想法)。
我在《巴尔的摩太阳报》工作时,天天很认真写文章,后来有位编辑离开报纸时请我吃饭,他说你当记者当得乖乖的,但他说:“Teams don’t trade for a single hitter.” 他意思是,就像在美式棒球里讲求挥大棒,我应该多写大一点的文章。
问:你后来离开报纸开始自由撰稿,如何跟不同的编辑台合作?
张彦:因为我想写这本书(《中国的灵魂》)。宗教书是我在90年代就一直想写的,如果我一直在报纸我没办法写,当然你可以请半年一年假,但那不太可能。
2010年我开始自由撰稿,可以花更多时间选题目,当然薪资不是那么稳定,我还是想做。从前我替《纽约客》杂志(New Yorker)写了文章,后来我觉得给他们写文章不错,他们是很好的杂志,但不可能每两个月就登一篇关于中国宗教的文章,他们没有那么多兴趣。
至于给报纸和杂志写,你还要看到不同编辑的要求,每个杂志报纸都有他们感兴趣的领域,特别是杂志,反而报纸比较自由,因为报纸需要很多东西,编辑不会天天跟你联系,但给杂志供稿的话,你一直会去想这个编辑要什么。编辑们有自己的期待,而自由撰稿人会去推想编辑会愿意登什么。我觉得杂志是独裁的(dictatorship),如果编辑对中国没兴趣,对印度、对非洲有兴趣,就不一定接受提案。
问:我以为这只发生在报纸上,有点朝生暮死。
张彦:报纸是更难,大部分的记者住在一个国家一段时间,2年或10年,他们把这段时间描述,做成报导,这也没错,但你住在那个国家的那段时间,不一定是重要的一段时间,或你住的时间是两个时间,头5年可能重要,后来可能不重要,这是很任意的时间选择。
问:你怎么避免这个状况?
张彦:找一个你想要写的主题比较重要,而不只是写出你的经验。以我的例子是“宗教”,其他人可能感兴趣的是建筑或城市化(这在中国也是很有趣的)。
问:你每天写作吗?
张彦:我不一定每天写作。我每天工作,但不一定写作。拍照、录音,以写下很多细节。我回去趁印象还新鲜的时候,尽可能多写一点下来,因为怕六个月之后要写书的时候,就想不起来了。我也会拍几张照片提醒自己,这很有用。我会取得对方许可,拍下照片,用手机拍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