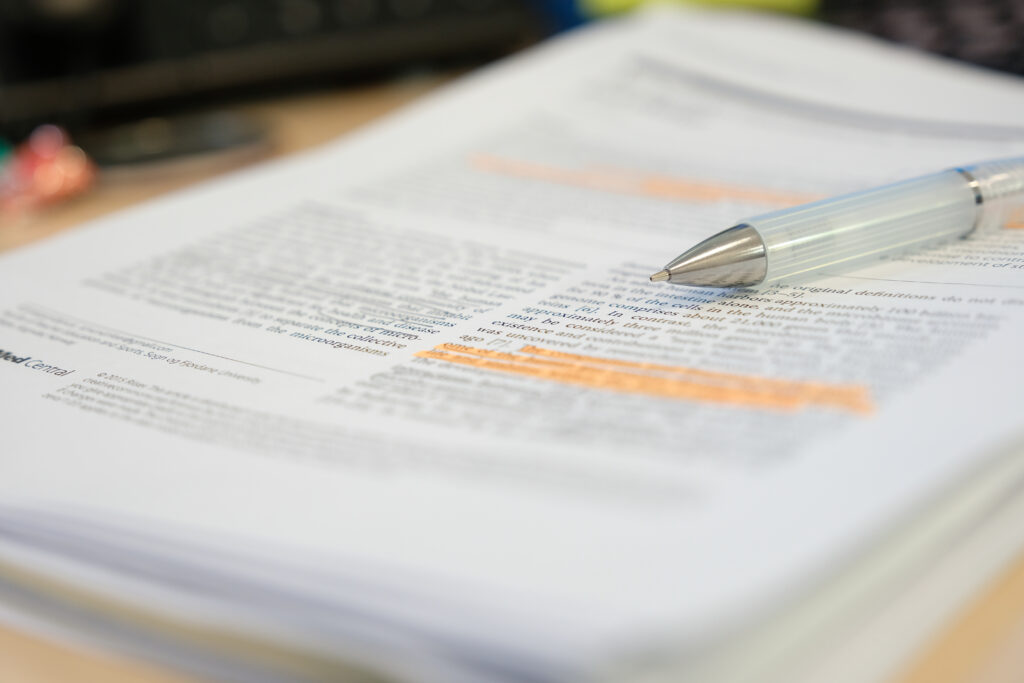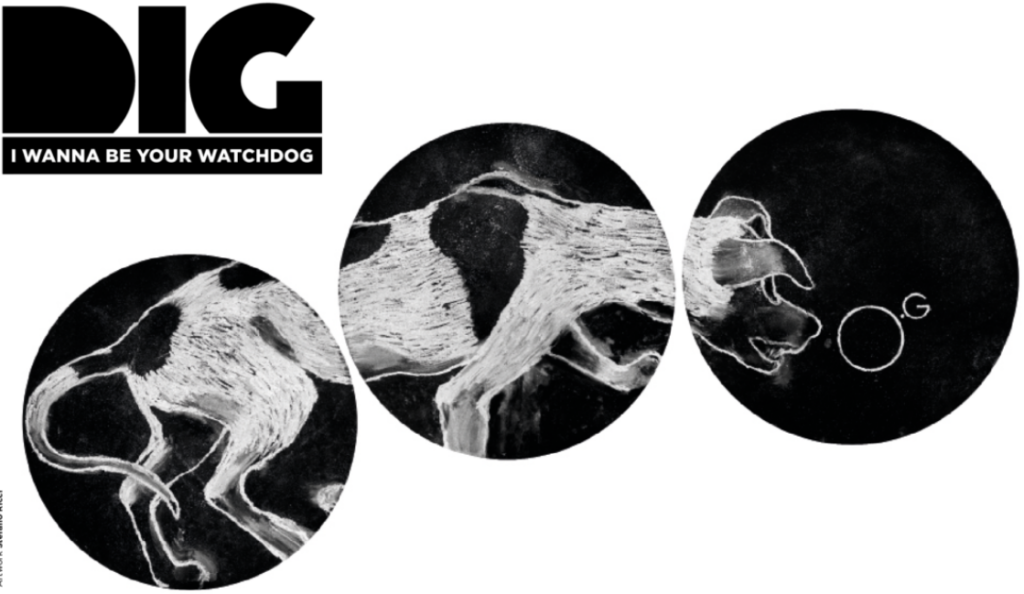2016年,宁卉在莫桑比克采访。(作者提供)
编者按:本文作者宁卉是端传媒国际新闻主编,曾从事国际报道多年,本文是宁卉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文稿,首发于内容社区 Matters,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编辑转载。
记者常常隐身在媒体后头,成为现有规则与建制的一部分;但也有很多时候,恰好是那个反建制的力量——既透过采访和写作,试着去破解身周权力纽带,又透过这些实践,试着在大众媒体这一媒介上搭建出新的规则。
我没有赶上一个可以从容地成为既定规则一部分的时候。想像中,新闻学院毕业后,踏实的新闻专业在那里摆着,有师父领进门,有一个记者理应的样子来激励。但我却没能往这个理想状态上靠拢。今天,仍能撑在“记者”这个职业,有时觉得真的是因为我的一厢情愿。
幸运的是,坚持一件事情久了,就会遇到很多同伴和前辈,就能一起继续下去。最近,我静下心来回想了这几年对我比较有意义的几个阶段。聊聊我是怎样毫无指望地离开非媒体的工作岗位,从寻找进入媒体的方式,一直到今天大约能够描绘出:“我是一个怎样的记者”。
从 Fixer 开始
2013年夏天,我从就职一年多的一间国际 NGO 乐施会辞职,停了在北京房子的租约,把行李处理掉,然后把自己丢在了一间破烂的酒店里,还记得房间里空调漏水、厕所的气味很难闻,一时失眠了,觉得无处可去。
那个晚上,我收到了一封邮件,朋友的朋友是一位美国记者,正在找一个能在那个夏天帮她的 fixer,问我是不是认识合适的人选。我激灵一下秒回,我认识一个很适合的人选——我自己。
当然我辞职就是想做记者,很巧合的是在下定决心要做记者的那个时间点,我遇到的题目,便是跨境的国际报道。
合作的记者现在已经很资深了,不久前回到中国驻站,但当时她还是美国一家新媒体的年轻记者。她申到了一笔来自一间国际新闻中心的基金,做的题目是中国的南水北调。她是华裔,但当时还没有很多的中国经验。
“fixer”,就像字面意思那样,是那个能够帮你搞定一切的人——在新闻界,他们是帮助外国记者完成各种采访任务的人,通常都是本地的记者,从找线索到找信源,从旅途安排到采访翻译,无所不 fix。出于种种原因,这些大型媒体机构大多不会直接让这些本地的 fixer 成为签约记者;总部的编辑与自家记者紧密联系,这些记者再在现场与 fixer 一起去寻找那个语境里的故事。
现在回想,理论上,我也许不是最适合这个题目的 fixer。中国有一些以为外媒记者 fixing 为职业的 freelancer(自由撰稿人),他们人脉广泛,熟悉外媒、也熟悉中国(但比较贵)。我则是一个刚刚从国际NGO离职、虽说在香港念过新闻学院、但媒体经验几乎为零的 newbie(新手)。还好那位记者当时也很年轻,大概感觉到我会很努力来做这件事情、感觉到我不会太计较为这一份任务作出的得失,她便给出了一份信任。
我们两个有些莽撞地在中国做了好几个星期的采访。她是拿着记者签来的中国,除了去到几个关键的工程沿线现场,我们一路理直气壮,竟也敲开了从地方到北京几个关键政府机构的大门。这篇报道后来也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一个奖项。现在觉得自己当时很幸运,我没有在这份突如其来的任务上撞得头破血流:在中国帮外媒做采访,多容易撞得头破血流呀?
那时,我很高兴在无处可去的那个夏天有这样一份尝试,并且与她成为朋友,一路来都可以在记者这个职业上相互鼓励。其实,这份经历还给我种下很多有益的种子:一是,相信直觉、信任你的伙伴,这份信任可能需要你 take a leap of faith(大胆一试);二是,即便莽撞地闯进去也有好的收获,这是对我自己 take a leap of faith。
最后还有,那一程下来,我大概确认了,除了参与报道,我更渴望拥有写作的权利。换句话说,我不愿再做别人的 fixer 了。其实这位记者有在报道最后给出我的名字;但对我,这不只是署名的问题,而是对搭建叙事的权力和能力、对实际手敲键盘写出故事的一种欲望。
做个跨境记者
三年前。2016年,我第一次尝试申请新闻基金来做跨境报道。具体的缘由有些忘记,应该偶然知道了一个环境机构在支持来自中国的记者,去非洲几个国家做林业相关的调查。我最终得到支持的题目是中国在莫桑比克进行的木材交易。
应当没有记者不是以抵达新闻现场为职业追求的,只是越来越少媒体愿意/能够支付这笔不菲的费用了。一部分旨在鼓励记者发展的基金,便会开设一些“grant”(拨款),支持一小部分有明确计划的记者去实现他们的选题。另一些有更明确议程目的——比如气候变化、环境保护等等——的机构,也会试着透过支持记者采访的方法,来推进机构自己的议题:有时是会组织一整个媒体团,有时也会拨一笔钱支持记者个人。
当然,收取各种基金的支持来做新闻行业的深度报道,可以引发一系列道德层面的讨论,以及各种机制对专业主义和独立性的保护,这里就不展开了。
这个时候,我已经做独立记者一段时间了。南水北调那个夏天之后,我在欧洲念了一个公共政策、偏国际政治经济的硕士;这期间,以各种我能找到的方法,给中英文媒体撰稿。那时我也接一些政策或舆论咨询报告的撰写工作。
但是我对记者的想像之中,已经有了一个去到现场的需求——并非突发现场,而是声音嘈杂的、日常的现场。但当然也不是任一地方,而是某个地方的某些人的生活,正在被一些看似抽象的、不可逆的、远远大于他们个体生活范围的趋势裹挟着走,我既好奇那些人眼里看到的现实,又好奇他们的这些“声音”是怎样形成的?而如果我去到那里,找到他们,并把这些都写出来,那么也许有更多人有除了那些“抽象的”、“绝对的”方法以外的,更真实的、片刻的故事,来理解今天看似很难看懂的当下。
当然,如果我现在去敲打2016年的自己,我肯定说不清为什么;但我很确信我想要去到那些地方,好像那是我要继续做一行、非此不可的路径。莫桑比克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满足了这一想像的题目。
盯着地图上的莫桑比克,我依然必须得找个 fixer。一番搜寻下来,我最终合作的伙伴,身上充满了我几年前的那一丝不甘。他本身是很好的记者,十分讨厌“fixer”这个称呼,但是实际上,各路外国媒体的 fixing 需求,的确是很重要的、真正能给他带来收入的机会。
我试着说服他,说你调查莫桑比克林的木业也很久了,但从未有过来自中国的input,我不只是那个聘请你的协助的人,我们也许能一起发展出很多新的理解?毕竟在这个议题里,中国是持份方,不是局外人。
他是很熟悉莫桑比克的,我们从南往北一整程,若没有他的人脉根本不可能做到;但另一方面,他从未接近过的中国社区,我却能够有所接触。可惜的是,我虽然收下了因他的资源而得到的“好处”(我的文章最后供给了《卫报》),他却未能因与我的合作有什么职业上的收获。换句话说,这一次合作,没有超出外国记者+本地 fixer 的方式。
我不知道他最后接受这个任务,有几分原因是工钱,有几分原因是我说的这种“合作意识”。但我是没有说服我自己的,这次的经历,也给我种下一颗蛮重要种子:明明己所不欲,为什么非得继续雇佣“fixer”的做法?
另外,这一程走完,印象很深,我跟他挥手再见的时候,他回到了莫桑比克北边的一个海边小镇上,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丝庆幸,庆幸我没有一直扎在中国。这两次很明显的“跨境”报道的经历,大约给出了我在记者这个行业中,比较渴望的那种样子。
我不是没有其他尝试(纪录片、突发、直播、名人专访等等),但鉴于我什么都舍不得:舍不得不自己去找题目,舍不得不自己去做初始研究和提出问题,舍不得放弃现场,舍不得不去对话(我甚至经常舍不得请AI或人工来替我整理采访录音),更舍不得自己在有了这一切准备和采访之后,能够去寻找书写的方法,决然舍不得放弃一个问题的复杂面向⋯⋯因此,到目前为止,透过极小的团队合作,以我作为一个个体记者的视角,用重现场、长特写的方法来写故事,并且能隐约指向更大的讨论,依然是我能找到的、我最有动力继续下去的“媒介”。
我自己,去画一个没有疆域、或是跨越了疆域的世界。
跨境,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背景。而且,新闻作为一个 sector,一直有跨境的基因在里面。我的博客名叫“hunger for awareness”,来自念新闻系时读到一本关于新闻业历史的书,谈起电报技术真正打开了新闻,因为人们能够立即获得千里以外的即时信息:技术带来的这个可能性,给了大众一个对认知和对信息的饥渴。
跨境报道的兴起
也许是一系列的机遇,或者我其实是个很有决心的人,从莫桑比克之后,我大大小小的采访,清点一下也有发自20多个国家,其中也有一些是找了基金支持、能够与当地记者一起合作的,但没有再去给任何明明是记者的同行安上一个“fixer”的角色。大多情况下,合作的记者都能够使用我们一起发掘的素材,或者最终的稿子我们联名发表,或者他们能给当地的媒体写稿。
跨境合作,早早地就是更能准确形容我工作方式的定义。
这些年,我依然生活在欧洲,身边同行的讨论中,“cross-border journalism”这个词,开始变得非常流行。这个流行有一些背景,我试着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观察,当然要disclaim一下,这些观察都非常主观、很不完整。
简单地说,在全球化更为深入的这个世界,我们都分享了利益也承担了后果。以往报道国际新闻的做法并没有在迅速回应这个变化。全球媒体的转型催生了新一批的记者,这些记者,一边自救,也一边也在改变国际报道的范式。
一个契机是2015年的巴拿马文件,让跨境合作很有影响力地呈现在了公众视野当中:原来调查报道是可以上百个国家的记者一起来做的!后来,人们也多意识到,巴拿马文件本身的曝光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案例。但是这个契机不是偶然,而是全球政经巨头利用金钱的全球流动勾连已久,必然会爆发的现象。回到新闻业,这打开了我觉得原本已经准备好了的跨境合作的讨论。
媒体人处在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之中:传统媒体的转型。许多报道方式和报道资源开始变得稀缺。比如,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“foreign correspondent”的方法论,尤其很多时候、不合理地“利用”fixer的做法,开始遭到很多的挑战。
最明显的就是大家对“parachute journalism”的批评了。所谓“降落伞”式的记者,尤其是在遇到突发新闻的时候,被以西方媒体为主的大机构空降到现场,有的不了解状况搞乱事实,有的则极度依赖当地fixer却不给对方足够的credit,还有很多被迫困在专门安排给外国记者的酒店里头的……批评声音四起也是很合理。
最近在柏林,与一些同僚谈起,说这些年,读《经济学人》实在有些索然无味;然后讨论说,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?那个所谓的“全球化初期”的时候,《经济学人》的文本给出一个看似完整、包罗万象的全球政治经济生活的图谱。而今,我们已经不满足他们做出的那些、很多时候大而化之的解释了,其中很大的原因,也许正是因为这类媒体,用是重编辑、弱采访的方法——毕竟,这些媒体的编辑们再有资历,他们的大多欧美中年男性的构成、从接受的教育到午饭吃的三明治都很相似,他们一边觉得自己可以指点江山,一边缺少对真实世界的持续追踪,最终避免不了的会同质化。
我认识的一个欧盟内部数个国家的记者的跨境合作,就是因为大约五六年前,大家就开始看到,即便是欧盟的一体化程度,彼此的偏见和误解,实在太夸张了。欧盟一度是全球化主义者向往的样子,大家都看到今天欧盟的问题;扩大到全世界,全球化加深了的裂痕,就更明显、也更严重了。
最后,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,那就是各种新媒体一边兴起、一边在报酬上不合理对待记者尤其是独立记者这个群体(当然撰稿人与媒体的那些事儿,又是另外一个话题)。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,出现了一大批没有得到传统媒体资源的年轻记者——他们可能来自西方国家、也可能来自各个新兴的经济体、也可能来自那些所谓的“新闻热点国家”,在技术的加持下,在缺乏更为具体而复杂的叙述的时候,在更多的竞争和更少的资源下,大家很自然地想要提出新的做法。这个讨论里头应该也有大型媒体机构的加入,但我自己的经验,年轻记者之间、一些相对比较理想主义的新闻机构或基金,聊跨境合作比较多。
当然,跨境报道有无数种做法,很多时候并不是像我这样非得跑去一个具体的地点,也绝对不局限与传统媒体会划分出的“国际新闻”这一板块下。跨境合作给出的效果也很不一样,有的更多是展示出同一个问题的普遍性,有的能够将一条产业链在不同国家的持份描绘出来,有的带来对话,有的则还是聚集在解释层面,当然也有很厉害的调查。今天提到的这些,还是局限在我个人的经验下的。
在自我质问中走下去
一个月前。2019年3月,我第一次踏上南美大陆做报道:目的地是一个小国家,厄瓜多尔。跟我合作的记者其实来自哥伦比亚。一起做这个案子之前,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在一个全新的、离开哥伦比亚这个特定语境的地方来做调查了;而在这个案子之前,我可能也有些过分地习惯与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做报道。一番采访下来,我俩都有一些反思。
一开始,很明显的一个担心:对他来说,一个厄瓜多尔的故事,两个外国人,能找得准吗?对我来说,除了“中国视角”(选题涉及中资),我去到这个语境中,是否有明显的意义?我是不是也成了一个“降落伞式的记者”?
我是一个很容易被自我批评绑架的人,这样的拷问在我脑海里很容易就没完没了:除了所谓的“中国”视角,我身上还带有任何其他的价值吗?我是会一直寻找中国以外的中国故事,还是希望最终能去做不非得与中国相关的题目?我希望谁来读这些故事?我作为记者,为谁而存在?是特定的一群读者?还是抽象的广泛的公众?他们不理解或不赞同我在议题上和书写上的选择的时候,我该怎么办?
这些问题我都还没有答案。但是在离开厄瓜多尔的时候,我和合作的记者都还算是content。我们狂奔两周,见到了很多人,另外还敲开了部长和中国公司的大门,让厄瓜多尔本地的调查记者觉得不可思议。一番下来,一起合作的记者也对于他冒然“闯入”一个新语境安心了许多,在有限的时间下,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素材,也让他对自己的语境——也就是邻国的哥伦比亚——多了一些参考和反思的余地。
这两天,我在梳理这些素材,意识到它们的有多“raw”:很多内容若不是我们到了现场,几乎没还原的可能(当然,我指相对的、而非绝对的还原)。在这个故事里头,几个利益相关方,就像是活在自己的山洞里,紧紧拽住自己最核心的利益,一厢情愿地构建符合这个利益的“事实”——大约因为我俩是外国记者,又是以相对开放的心态,一视同仁地采访,才抓住了好几个“事实”。由此,我们书写出来的故事,也许能让读者心里的“山洞”更宽广一些。
说到底,记者的素养在于寻找、分析和讲述。不管什么行业、社会、文化,对于常常像一根针一样扎进去的题目,这些素养都是很有效果的。这一层效果,在进入一个全新领域的时候最明显,扎深一段,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了——但那又会培养出另外一种记者形态,在一个领域深入的、或是在一个范围内精密调查下去的。这个时候,我相信,记者这一职业的其他特性又会冒出来。
当然这跟选择的题目也很有关,我常常看到有记者想去陌生国家采访,一来就带着一个巨大的命题,这样的话,有时会让现场无意义,因为你带去的大题目本身已经是完整的讨论了,现场一不小心就成了辅助,是为了印证讨论;有时则会被大题目必然会有的复杂回应,弄得一团糟,自己还未有能够理解的路径,就被现实给轰炸了。
也许你像我一样被批评和自我批评困扰,讲到这里就忍不住质疑:那你这样东奔西跑,难道不会觉得自己的认识很肤浅吗?难道不会跑着跑着就没地儿可去了吗?你跑十年之后,又留下什么?
这些问题我都质问了自己很多年。但最近略微放宽心,我发现,我每每看到一个新鲜的事情,总能提醒我回过头去寻找和联系一些已知的、恰好可以串联起来的思考面向。而我积攒的这些面向,又必然会在下一个旅途的报道和写作中呈现给读者。我的成长,也许会完整地体现在我的作品中:任何一个创作者,如果你告诉他/她,你的作品一定有进步的空间,我想他们都会是很高兴的。
也许我在每一个站点待得都很短,但这些短暂但激烈的停留,恰恰都在重度地挑战我的直觉和逻辑:两者相加,也许是记者这一行能给一个人最好的经验。而且,常常因为迈出了进入陌生环境的第一步,而找到了更好的、可以继续下去的新的线索。我也尽量让我的书写不被一时一刻的情绪带走,最近翻开自己一两年前的故事,甚至觉得有一些也还挺可读的,没有“过时”。
这些年,聊媒体从业困境的人更多,但是我依然觉得,缩小到个体身上,成为怎样的记者?——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多不同答案的。2011年,我在离开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的时候,也觉得自己没有答案,便去了我感兴趣的女权主义议题、去到国际 NGO 里头做些尝试,结果,这些经历,最后竟然也把我带回了记者生涯。
有的决定以“关上一扇门”为主要后果,有的决定却能替你打开更多的门,祝大家做更多打开视野的决定!